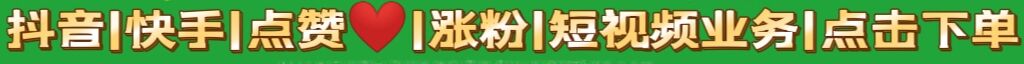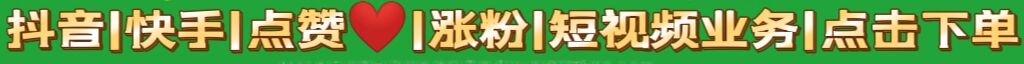陈洪绶(1598—1652),浙江诸暨枫桥人。字张侯,号老莲、莲子,后号慧池,新号福池、老池,又名云门和尚、九品莲台师等。性格傲慢,性情狂野。他以酗酒和沉迷于女色而闻名。他的自控力极低。但作画时,他却全神贯注,时刻控制着手中的画笔。他跑得很慢,就像蚕茧吐丝一样。细腻均匀。作为中国绘画史上杰出的画家之一,陈洪绶在明清时期是独一无二、无与伦比的。鲁迅先生对此给予高度评价,认为“老廉的画是一代人的杰作”。
翻开明末清初画坛,陈洪绶是绘画史上不可忽视的独特人物。其绘画风格对后世影响深远,影响了百年中国画坛“海派”任熊、任逊、任毅等著名画家。他的所有绘画风格都继承了他的传统;现代艺术大师徐悲鸿的人物画,运用了陈画简洁有力的特点和水晕、暗印的技法;白石老人的人物塑造也吸收了陈老莲的表现手法和夸张手法;国画大师谢稚柳早年的书画艺术也受到陈洪绶的影响。当代画家程十发也将老莲的独特之处引入到审美艺术和民间艺术中。
清代张庚在《潮代中国画志》中论述:“洪寿所画人物,躯干雄伟,衣纹清晰圆瘦,有公林、子昂之美。色彩设计以吴胜法为基础,其气势和气势,是那么的正直,胜过明朝的徐钦三百年。朝在《明代画录》中也记载:“红寿长于图,一笔而作,与鲁谈微(晋)相似。画历史事件时,容貌、服饰必须与时代一致,作品才能区分。”由此可见陈洪绶人物画的至高境界。陈洪绶的人物画大多是他所画的人物线条清晰、圆润、细细,又稀疏、宽松,服装线条细细、圆润、圆润。保持“转变”境界。服饰图案的处理具有很强的装饰性,色调淡雅,风格刚健,尤其是笔法细腻夸张的山水作品,颇有古人的花鸟画意。虫草勾勒细腻,色彩鲜明,明快,用笔由方边转向圆边,用简洁凝练的线条和色彩描绘飞舞的蝴蝶和鸟儿、蜜蜂和蚱蜢、芭蕉叶等。花蕊、玫瑰、兰花、菊花以一种平静而微妙的方式呈现。笔墨流畅,流畅。滴水而宽敞。
陈洪绶中年时的人物画堪称精湛,晚年更是精进。这一时期的人物画更多地表现世俗风情。 《秀雅如画》画的是抄写员倚在石桌上,仔细观察女子做针线活的曼妙身姿。书房的四件宝物,就放在石桌上。所绘人物饱满古朴,线条沉稳刚健,轮廓细腻,色调淡雅,略显与其夸张的风格不同。他用细腻、工整的手法来表现人物。人物衣服的轮廓圆润柔和,他所用的线条有一丝金石相间的感觉。手掌的画法也不落俗套,多用重笔、折石勾勒、侧笔、干笔等。墨的密集拓印体现了对笔墨的掌握。
《雅集图》的文字以白线勾勒,线条圆润细细,笔墨纵横。人物五官、脸型绘制准确、简洁,有起伏感。这体现了陈洪绶高超的造型技巧和细腻的笔触。力量。陈洪绶54岁时写的48页《博古野》,选了春秋至秦人17人,汉人22人,晋唐人9人,著名历史人物故事共48个。主题是贫富与人格的互动关系;该哲学融合了司马迁史家的客观思想和儒家儒家的主观思想,用其中极其丰富的生活各方面来表达他一生中的无限情感。这是他去世前一年的最后一部作品,造型、笔触都十分精美。
纵观各种对陈洪绶作品的赞誉,绘画中常用的形容词有“古”、“奇”、“高”、“仙”,意思是他能与古人交往,达到继承传统的最高功力。 ,同时又能够出人意料地创新,格调高雅,气度不凡;同时称赞“张侯书法高雅”、“集古诸家之思想,自成一体”;诗文“雅致,有诚趣”。
陈洪绶晚年的山水画大体有两种技法和风格。一种以唐宋勾法为主,稍有夸张,风格古朴,装饰趣味浓厚。一种融合了勾、拓、渲染的手法,融入了元代的笔法,古朴中蕴含着笔法的含蓄含蓄的神韵。 《秋林侧杖图》中的树石画法,体现了陈洪绶晚年的笔墨特点,即由中年时期较为方刚刚健的风格,转向方圆结合、较为圆柔的风格。魅力。图中岩石若以麻缠、折条、横裂相结合的方式划出,用干笔擦出裂纹中的条纹,墨色凝结柔和,与王的笔法颇为相似。孟与倪瓒。树木的纹理不只是局部坚硬,而是浑厚的纹理和轻盈的纹理相结合,赋予树木更加圆润的感觉。图中人物画得圆润优美,转笔时没有任何锐角。
陈老莲在色彩的运用上也有自己的特色。他的淡色与重色同时运用,浓而不滞,淡而不薄,淡雅而古朴。特别是,使用诸如蓝铜矿、柠檬绿、朱砂和白色粉末等矿物颜料来赋予它们装饰性。他考虑到色彩不能损伤笔墨、墨水不能浮在色彩上的原则。如他后期创作的《玉堂柱图》,衬托玉兰的太湖石,上下较大,细腻清晰,用笔扎实,多为轮廓线条。曲、尖、直,突出地呈现了太湖石的形状和品质。
陈洪绶的一生经历了坎坷曲折。他9岁时失去了父亲,18岁时失去了母亲。他屡次尝试却屡屡失败。不得已,他卖掉画作攒钱,考入国子监。然而,当他看清政府的黑暗和腐败后,他走开了,躲进了父亲的朋友、著名书画家徐渭的“常春藤书店”,在那里吟诗作画。当清军入关,明朝灭亡时,他为自己不能忠于国家而感到羞愧,但后悔已晚,故自号“悔赤”。
为了拒绝与腐败势力合作,避免被清朝追杀,他出家为僧,潜心于书画创作,永远逃离了功名思想。他的人物画充满了夸张的色彩。在艺术形式上,他表现出追求怪诞的倾向,即在形象的深刻提炼中,既注重形体的夸张,又注重表达的含蓄表达。他向古人学习,但不拘泥于既定的方法。他注重领悟古代画法的内在精神,大胆突破以往的成规,融会贯通,独创而独特,其艺术效果具有一种傲然古风。被称为“古奇之物”。晚年画中的人物形象夸张,有的作品形象异常怪异,以凸显人物的性格特征。
19岁时为《九歌图》创作了11幅木刻插图。他创造了自己的形象,却又无可奈何。他用历史故事来表达对乱世的哀思和对国家、对人民的关心。这是他早熟的艺术天赋的体现。古树野花、怪石蜿蜒的小路的简洁轮廓,以及大片留白的随意铺贴,营造出山中古道荒凉、荒凉、孤独的意境。它有力地渲染了屈原流亡、孤独的环境。它还注重人物的塑造。屈原皱着眉头,面容憔悴,胡须下垂,目光高远,显示出他不屈的性格。正是这种夸张手法塑造的屈原形象,奠定了陈鸿绶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。后来精品不断出现,继续发展了《九歌图》的夸张技法和风格。在《陶渊明归来》的“解封”部分,陶渊明被画得比较高大。作为陪衬,他身边还有一个对自己的职位十分觊觎的矮官。他弯着背,双手接住陶渊明的右手。被去除的官方印章。这和他常用的夸张手法,让人物的头大得出奇是一样的。通过形体本身的对比效果或造型之间的不平衡,突出表现人物的精神气质。
陈洪绶生活在明清革命时期。中年时期,陈洪绶仕途遭遇坎坷,但艺术名气却与日俱增。面对自己不想当画家而社会却要他当的现实,他只能用特殊的疯狂行为来反抗。然而书法却给了他精神上的慰藉。陈洪绶虽然不以书法闻名,但他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却是相当惊人的。陈洪绶在写作时严格遵循中心的写作方法。他深谙直掌平腕写字的秘诀。虽然他偶尔会用侧击来攻击严的位置,但他很快就能调整笔势。如此高超的控笔能力无疑只有手掌直立、手腕平放才能持笔。
而且,他在书写过程中的“回藏区”、“提按”、“停顿”、“扭腰”、“回响”等书法所要求的击键似乎也没有任何瑕疵。写作。只是他做的毫无痕迹。 ,这也是外表朴实、信仰言语不美、修身至善境界的具体体现。从陈洪绶的笔下,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写作心态是一种愉悦、宁静的状态。轻松、快乐,写作的过程对他来说似乎是最甜蜜、最舒服的享受。因此,可以说陈洪绶找到了书法的最佳运用方法,而这种方法就是书法的“真谛”。曲折也是为了行文流畅,营造美感。
(取自互联网)